赵汀阳:道的可能解法与合理解法
江南app下载-官方网站 整理赵汀阳
2011-09-29
对经典的解释需要什么样的创造性?
先说个故事。在1993年第6期的《社会科学战线》上,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老子《道德经》第一句话的解释问题的短文,认为“道可道非常道”的现代流行解读可能是错误的,并且试图论证“可道”的意思不是“可说”,而应该是“有规可循”的意思。2010年10月,我有幸与裘锡圭先生一起参加在布鲁塞尔的 “中欧文化高峰论坛”,其间裘锡圭先生说他看过我的那个“新解”,并且与我分析讨论了老子的这个重要命题。裘锡圭先生是古文献学大师,他的分析使我多多收益。简单地说,假定我的记忆准确的话,裘先生认为,从春秋战国当时的语言惯用法上看,作为动词的“道”确实多指“践行”之意,但也不排除“说出”的用法,他揣摩老子的语气,认为老子开篇时很可能想要点明他要向人们讲述的深刻思想并非一般俗论,据此,“道可道非常道”很有可能说的是“我这里要说的道,可不是通常所说的道”。一个理由是,《道德经》通篇都在言说老子心目中的道,显然,道并非不可言说,否则与《道德经》所论就互相矛盾了。裘锡圭先生的这种解释颇有吸引力,尽管他也采用以“说”去解动词“道”,但与流行的解法大不相同,流行解法讲的是“道是不可说的”,而裘锡圭先生讲的是“道是可说的”。关于“道是可说的”这一点,我完全同意裘锡圭先生的看法,不过,这个解说更适合作为老子整个文本的潜台词,似乎并不是针对“道可道非常道”这一命题的直接解读,因此我仍然愿意保留我的解法,我答应裘先生再对我的解法做些解释。后来又就此问题请教了我的受业导师李泽厚老师,李老师说,在目前存在的诸种解法中,他较为同意我的解法,因为比较符合老子的思路。重要的是,李老师同时指出一个问题:古典思想的生命力就在于我们总能够发展出多种有创造性的解法,我们只不过是力求合理的创造性解释,因此传统才能转换为当代。故事讲完了,接着说问题。我愿意以此短文向裘锡圭老师和李泽厚老师致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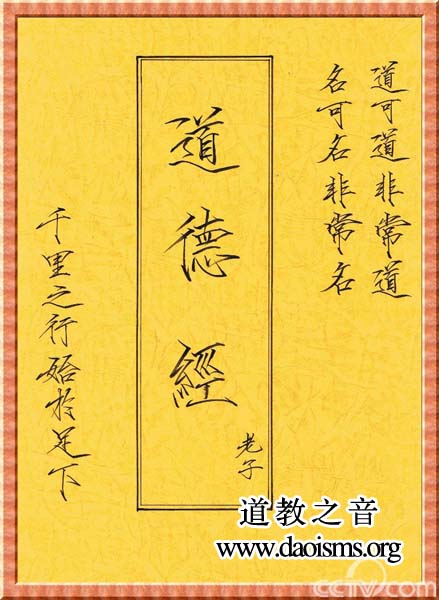 古典思想是我们可以开发的思想资源,有多少种合理开发的方式,就意味着古典思想有多少条通向当代之路。关键问题是,什么才是合理的创造性解释。所谓合理,应该是说,一种解释与古典问题具有明显的相关性(relevance),俗话称为“靠谱”;所谓创造性是说,一种解释能够在古典思想与当代问题之间建立新的相关性,在古典思想中开发出当代的有效性,使古典思想“增值”。比如说,我以“天下体系”去重思重构周朝的“天下”概念,就是试图这样去做的。
古典思想是我们可以开发的思想资源,有多少种合理开发的方式,就意味着古典思想有多少条通向当代之路。关键问题是,什么才是合理的创造性解释。所谓合理,应该是说,一种解释与古典问题具有明显的相关性(relevance),俗话称为“靠谱”;所谓创造性是说,一种解释能够在古典思想与当代问题之间建立新的相关性,在古典思想中开发出当代的有效性,使古典思想“增值”。比如说,我以“天下体系”去重思重构周朝的“天下”概念,就是试图这样去做的。
在这里,我愿意进一步讨论关于老子《道德经》第一章的解释问题,尤其是“道可道非常道”这个命题,它直接涉及对老子思想的整体理解,涉及对老子思想的定位,因此很值得深究。首先,我们可以采取一种比较开放的分析策略,对古典文本的意义解释不要求必然之论,而是允许多种可能解释;其次,追求某种“更好解释”(better interpretation)——可以理解为弱意义上的“更好论证”(better argument,哈贝马斯标准)——首先意味着,何种解释在古代语境中是更为可能的,这追问的是,古人更有可能说什么;同时意味着,何种解释对于当代思想而言更具建设性,这追问的是,替古人对当代人说什么才是更有意义的。按照这种标准,我们有理由追问:(1)在古代语境里,老子思想主要是一种关于知识问题的形而上学还是关于实践问题的形而上学?(2)老子思想对于当代问题有什么建设性的方法论意义?澄清这两个问题应该有助于更好解释老子的文本。
中国古人的知识追求与超验问题无关,基本上是以生活问题为界,即使是那些关于自然万物普遍原理的想象,比如阴阳五行之类,也是关于生活知识的艺术注释,绝非“科学”探究。可以说,中国思想中并无单纯关于“万物”(things)通理的形而上学,而是另外发展了一种关于“万事”(facts)通理的形而上学,思想重心不在万物而在万事,万物只是万事的相关背景,万物只是因为万事而具有意义。事情要一件一件做出来,因此,“做”的问题,尤其是“做法”问题,就成为中国思想的核心问题,道虽为万物万事之共理,但既然物之意义在事,因此,道的意义在于成为事理。当思想追问的是万事做法之通理,这种形而上追求就在本质上是作为方法论的形而上学,而不是作为超验解释的形而上学。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思想并不关心现象背后之理念,而是关心贯穿现象之中的道理,就是那种应万变而能守一的一贯之道。关于“万事形上学”(metaphysics of facts)以及“做事”理论的更详细论证可以参见我关于“我行”(facio)问题的分析(区别于“我思”,cogito)①,在此不多说。
道作为普遍方法论是可说的,而且必须是可说的,也就是能够思想的,否则又如何能够“知”道?假如道不可说,也就不得闻了,孔子又如何能够想去“闻道”呢?关键在于,在中国思想语境里,如何知道,这不是一个无法逾越的知识论问题,因为,道就在事中,道是亲近人而在的,而不是知识界限之外的存在或理念。确实如裘锡圭先生所指出的那样,《道德经》通篇都在解说道。老子详细地从生命的、生活的、政治的、社会博弈的、军事的等多方面讲述了道的原理。
当然,中国思想传统中也有关于不可说问题,但主要是关于美学意境的。美学意境确实不可言传,但这与知识论问题无关,而是对一种无限丰富的美学效果的追求,因为具有无限性的意象是永远迷人的。简单地说,作为思想对象的事理都是可说的,而作为想象力对象的意象才是不可说的,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至于佛教给中国思想注入了某种不可说问题,这是后话,与先秦语境无关。现代西方知识论的引入,尤其是唯心论和先验论,给中国思想指出了一个以前没有被关注的因而显得特别新奇迷人的超越领域,这很可能诱导现代人把老子之道解释为“不可说”之道。不过最后这一点纯属猜想,也只能是猜想,因为我们难以找到人们心里怎么想的证据。但可以注意到,古人关于老子的解释更多与我的解释相一致(后文接着分析),而把道看做是“不可言说”的,则多属现代解读。总之,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那些“更高的”(the higher)或“隐藏着的”(the hidden)万物之理的知识论兴趣非常有限,而更多地关注那些道不远人、亲身可即的万事之理,特别是政治、社会、生命和生活之理。所以说,道的问题不太可能是个知识论问题。
如果按照当代观点来看,老子的思想(连同兵家思想)蕴含着相当于当代博弈论的思想,甚至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博弈论,它与当代主流博弈论的思路既有不谋而合之处又有深刻差异。这一点意味着老子思想有着巨大的潜力。从整体上说,老子思想在广度上远远超出博弈论,可以说是一种对一切事理普遍有效的思想方法论。老子的思想有一个特别的优势,它采用的是动态互动模式去思考各种问题,当代思想的发展已经注意到,这种把动态互动的形势状态考虑在内的思维模式比主体性的或单边主义的思维方式更为理性、更有能力处理复杂多变的事情。按照哲学的说法,老子的思想模式从一开始就直接进入了主体间的(inter- subjective)问题而不是主体性的(subjective)问题,就是说,任何被思考的事物都是或者好像是一个“对手”(player)而不是一个“对象”(object),都是一个具有主动回应能力的事物,而不是一个被观察的被动者或者被主体的知识能力所处理定型的对象——这个问题说起来有些拗口,请原谅我多说几句。对象是一个“在场的”但却只是“被看的”、由我的主观性来做主的现象,而对手不仅在场,而且“在局中”与我互动,所以说,卷入与我的关系之中的事物并非一个为我所定、唯我是从的知识论对象,而是一个有可能与我共谋、或与我作对、或与我共变、或甚至改变我的存在方式的对手。因此,道要说明的是我与事物之间的互动创作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道是存在论意义上的(ontological)运作方式,却不是知识论意义上的 (epistemological)神秘对象。

- 《易经》艮卦为什么不谈“手”
- 富有地方文化特色的苏州玄妙观江南娱乐在线登录账号 音乐
- 中国茶道中的道家理念
- 神玉、礼玉与民玉,你是否了解手中玉器的真正
- 江南娱乐在线登录账号 文化:江南娱乐在线登录账号 时日禁忌研究(试读版)
猜你喜欢

 |
|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6208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6208号